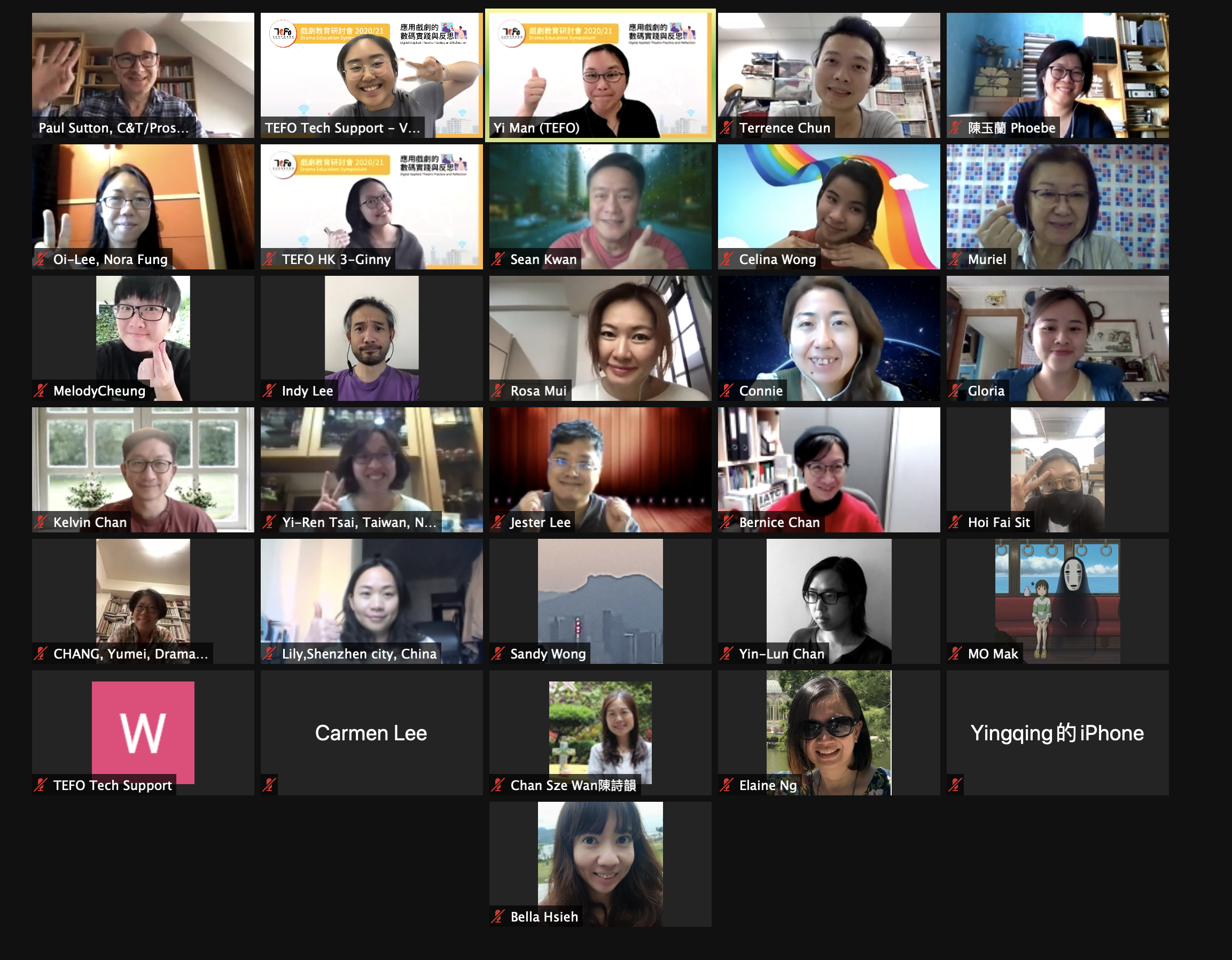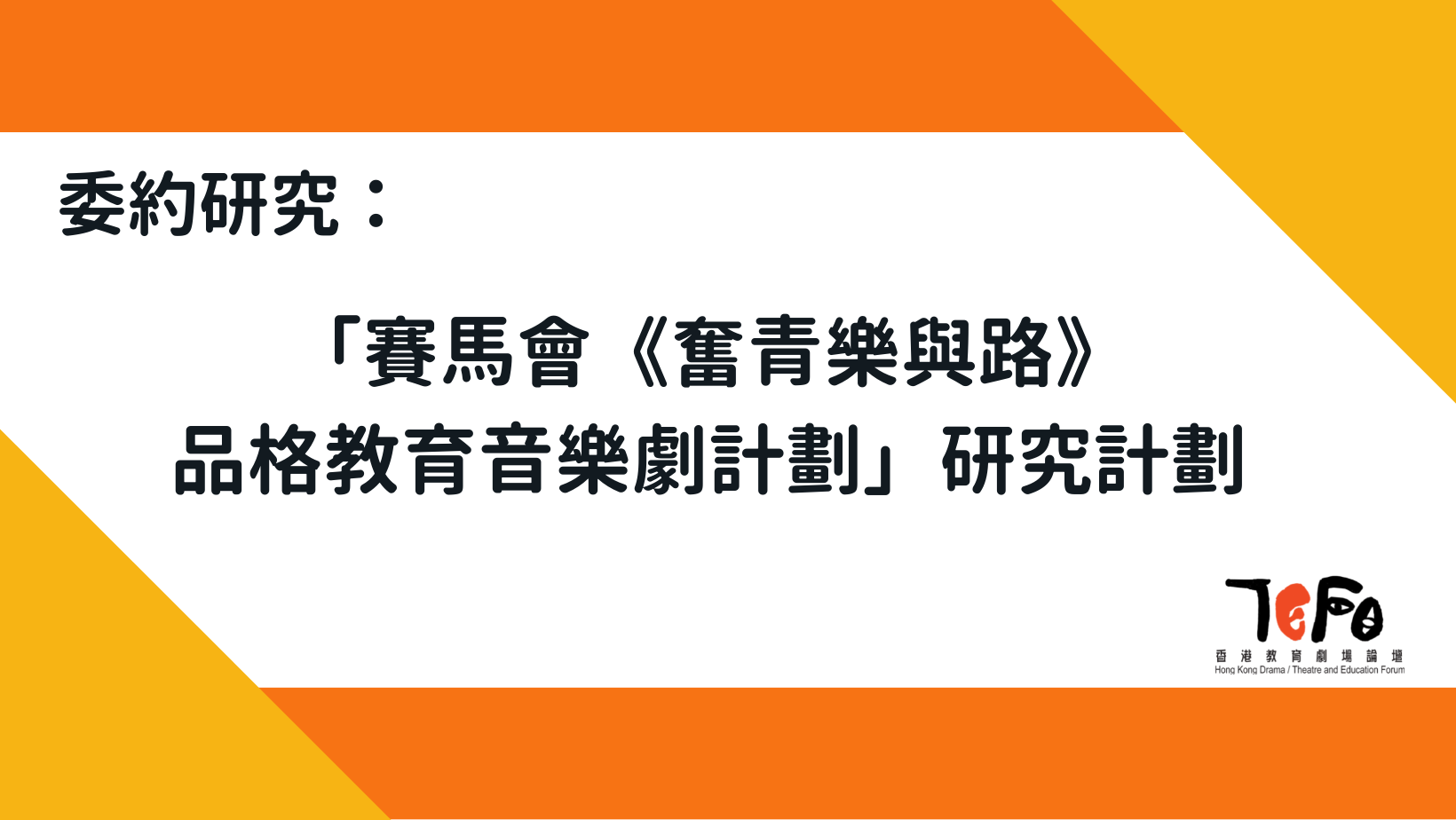有做研究經驗的老師或藝術工作者大概都知道研究工作並非單單依據一些工作步驟—包括界定研究問題;搜尋相關書籍、文獻做回顧;釐清研究問題、範疇和對象;設定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蒐集和分析資料—就自然得出研究發現。因為過程中研究者要整理、判斷和決定哪些資料相關,怎樣歸類和分析。各種大小不同的決定是基於甚麼思考和如何作出取捨?這些思考過程看似隱密不見;對不少人的來說可能是一個「黑箱」(blackbox)。
『其實,書寫能力能教的嗎?還是直等到學生的認知能力發展到一個地步就自然而然寫得好呢?』多年前,我在一所大學的研究及發展部們從事通識科課程研究工作,黃老師(化名)跟我們研究合作初期就問了上面的問題,該項研究合作計劃探討戲劇於通識科的書寫可發揮的作用。黃老師說中六學生有書寫的困難,他和其他科任老師曾試用不同方法刺激學生思考,例如給他們充份的課堂討論、用概念圖、好文共賞等。但他發現學生討論得興致勃勃,寫不出東西來的學生課後依然如是,或只重覆抄寫材料內容,了無重點,想法仍然不著邊際。
戲劇、思考和書寫
黃老師理解思考與書寫密切相關,但為何那些方法都不管用呢?巴西教育家弗雷勒(Paulo Freire)提醒我們:『學習首先是思考經驗,思考經驗是準確地思考的最佳方式。』(註1) 建基於這理念,經過商討,我們以欺凌為課題進行課程的行動研究。科任老師跟學生討論當時一樁陳巧文網上欺凌事件。(註2) 與此同時,我這邊廂就選取一首關於學校欺凌的英詩,以過程戲劇(process drama)形式讓學生入角成為欺凌事件中人去體驗和思考問題,旨在試驗戲劇如何協助提升這班通識科學生多角度思考,以及整理複雜豐富多元的想法成為書寫內容。(註3)
學生經歷兩個雙教節課堂的戲劇探索,入角成為戲劇事件中的欺凌者、同學、老師等不同人物。研究發現,學生普遍認為戲劇體驗讓他們切身體會故事主人翁阿Bill作為欺凌者的想法和感受。有學生形容過程戲劇的經驗猶如跟戲劇導師「一齊起樓」,戲劇提供一個架構,同學代入角色參與其中,一點一滴的建構戲劇人物世界。至於做家課,好幾個學生說可以參考的觀點除了自己本人的,還有自己代入的角色和其他同學扮演的角色的觀點。另一學生說平日只拿書本和筆記找資料答題,就好像站在高山向下望,模糊不清般辛苦。相對地,阿Bill的故事把欺凌情況具體化,以小見大。事實上,家課作業請學生分享戲劇活動對他們了解陳巧文的例子有否帶來甚麼思考/啓示。有學生點出兩者相同之處,例如兩個主人翁受欺凌皆因兩人都被視為「異類」、「破壞常規者」;也有學生指出兩者相異之處,例如網上欺凌沒有實質身體的攻擊行動,以及參與者真實身份不詳故可更肆意攻擊,對受害者的傷害更深。學生藉由過程戲劇提供的人物角度去探索問題,人物角色的視點加上學生離開角色後的思考成為寫作的點子和內容。
「提問式」教育深化思考
過程戲劇的行動研究到尾聲之際,我和黃老師都發覺需要協助學生深化學習。最後一堂,我請學生整理先前兩節的戲劇體驗,就「阿Bill和他的處境」和「校園欺凌」兩方面寫下自己的疑問/進一步的詢問(question),同時列出「欺凌是 … …」的理解。我們從旁觀察,學生把寫上想法和問題的告示貼逐一貼到黑板上相關的欄目。過程中,學生整理著自己所領會的、閱讀同學告示貼上所寫的、比較與整合不同觀點之間的關聯。就校園欺凌所提出的問題遠超出戲劇探索的範疇,包括:旁觀者在欺凌事件的角色,老師或同學在事件中能幫助的有多少。(註4)
專研詮釋現象學與教育學的范梅南(Max van Manen)指出教育學(pedagogy)本身是生活的一種模式,本來就與實際生活相關。他借用嘉達美(Gadamer)的說法來強調提問的重要性:『問題的本質是開啟可能性,並對各種可能性保持開放』。(註5) 弗雷勒更是倡議「提問式」教育(problem-posing education),他鼓勵有志的教師把人生於世所面對的境況以「難題」的方式提問出來,務求誘發學生探索現實狀況的意欲,不至把現況處境簡單的照單全收或視為理所當然。(註6) 顯然,這些通識科學生入角進入阿Bill的戲劇世界,誘發了對阿Bill遭遇和校園欺凌的好奇心,投入了「提問的心情」(a questioning mood)。(註7)
戲劇教育把莘莘學子生活經驗所未及之處引進學習體驗之中,「提問」的行動協助學生把戲劇體驗概念化。過程中,學生正學習開啟自己思考的「黑箱」。
註:
- 參閱 Freire, P. (1895).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 Culture, power, and liberation. Hadley, Mass.: Bergin & Garvey,頁3。
- 2008年5月,陳巧文在奧林匹克運動會香港區火炬接力期間高舉並展示雪山獅子旗,此舉被視為支持西藏獨立,引起媒體追訪。其後,她的個人生活和照片在互聯網上曝光,上傳和轉載,繼而遭到社會抨擊。黃老師及其同事認為這是網上欺凌事例,值得跟通識科學生討論。
- 參閱羅婉芬。2010。〈以「人」為本:教育戲劇作為受壓迫者教育學的實踐〉,載於 Cult通主編,《通識X文化研究》,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頁80-7。和 Chan, S. C. K & Law, M. Y. F. (2012). ‘Learning to write critically: Drama as pedagogy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cultural criticism’, The Journal of Drama and Theatre Education in Asia Vol.3, pp. 69-92. 全文下載:http://www.dateasia.tefo.hk/index.php/dateasia/article/view/28
- 就學生對「阿Bill和他的處境」和「校園欺凌」提出的問題和「欺凌是 … …」的理解,可參閱 Chan & Law,2012,頁81-82,91。
- 參閱范梅南(Max van Manen)著,高淑淸等譯。2004。《探究生活經驗:建立敏思行動教育學的人文科學》[Researching lived experience: Human science for an action sensitive pedagogy.]。嘉義市:濤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頁52。
- 參閱弗雷勒(Paulo Freire)著,方永泉譯。2003。《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台北市: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頁116-117。
- 參閱范梅南,2004,頁53。
標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