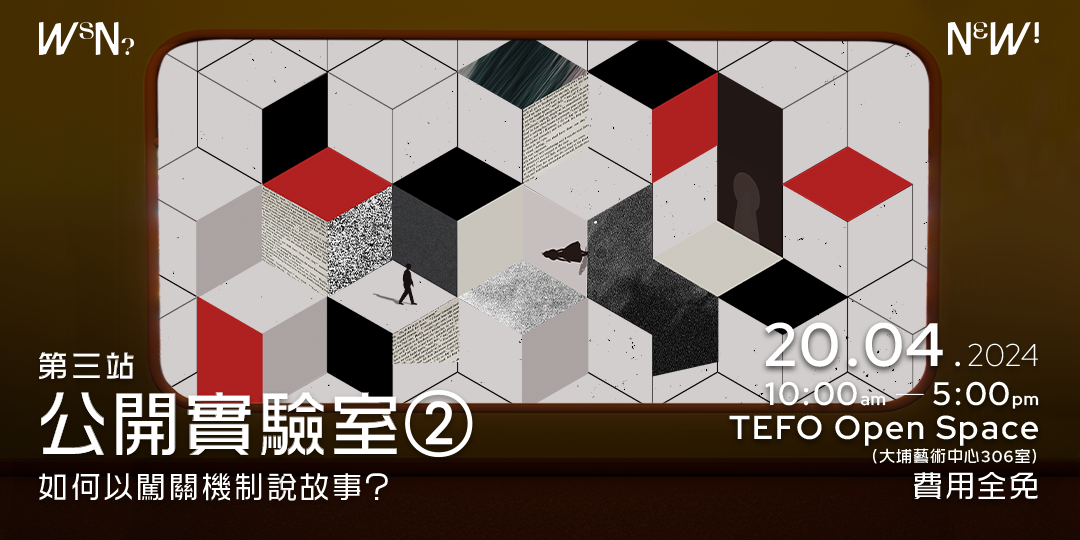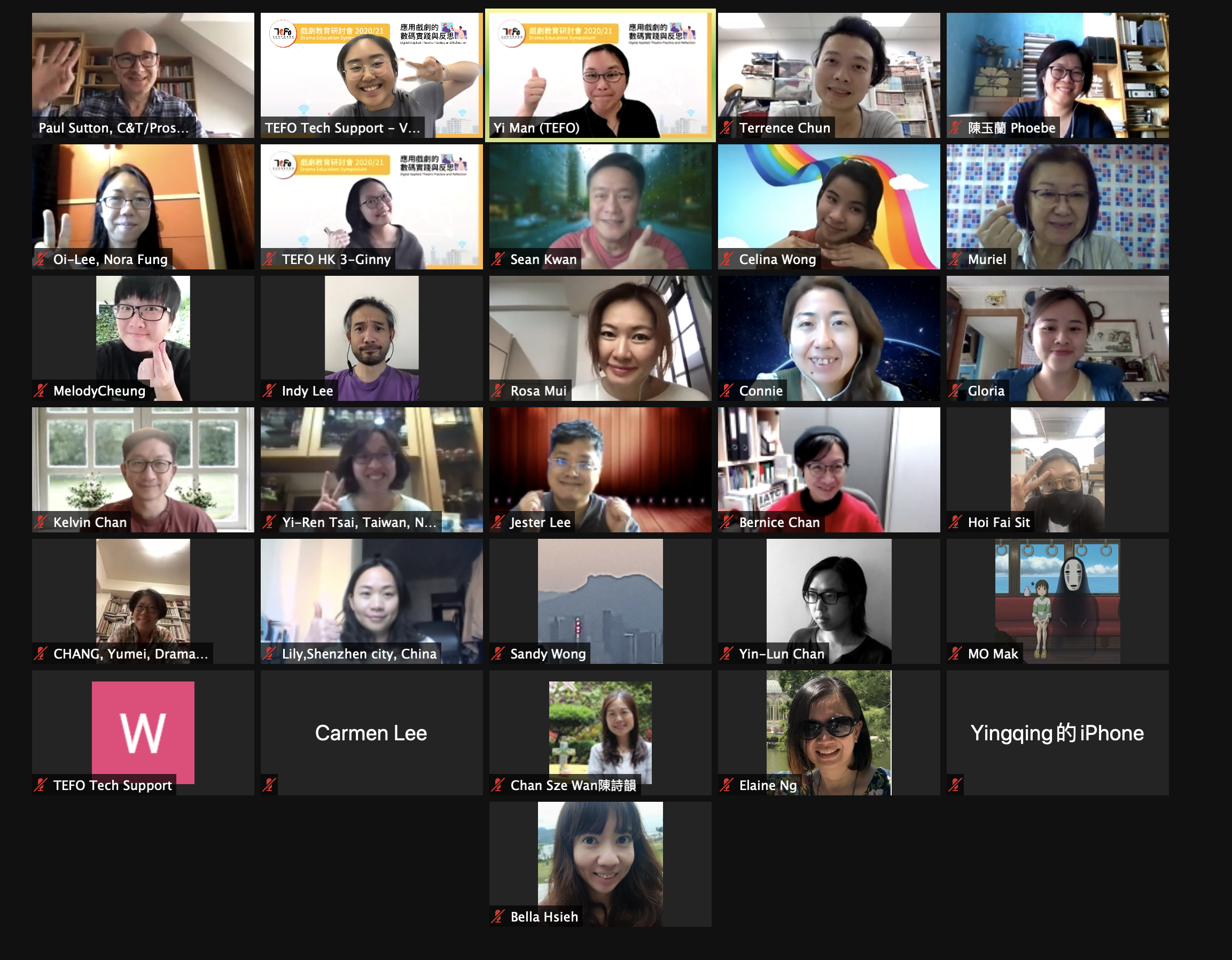2019年3月22至24日期間,TEFO與香港話劇團合作,舉辦了「HKRep X TEFO 應用劇場萬花筒」,期間邀請了不同應用劇場團體來分享他們的作品和經驗。活動後,我們也分別邀請了李嘉敏、吳文基及潘君彥分享他們對應用劇場演出的回饋。
《TEFO Edward Bond小組製作 Edward Bond 作品選讀《椅子》X 教育劇場示範體驗札記》
文﹕潘君彥(演員、戲劇教育工作者)

完場後,我的腦海中一直盤旋著工業金屬樂團Marilyn Manson 的大碟《Heave Upside Down》中《Say10》一曲。
“You should pray now, is it above, or is it below?”(你該禱告,向天傾訴,抑或地獄申訴?)
幾年前,曾經排演過同一劇作家(Edward Bond)的另一作品《The Children》,對作者的風格略知一二。儘管這是場讀者劇場(Reader’s Theatre)為主的應用劇場節目,黑盒內的歐式燈柱、燈光布局及雜亂的畫作,早早已滲出一種幽暗的氛圍。
然而,主持人陳玉蘭在介紹節目及劇作時,卻又是非常克制、冷靜,並沒有刻意撩動觀眾預期過度戲劇化的情緒之中。
故事發生在2077年的倫敦。我所預期的英國霧都,從樓宇內的房間開始破落;享有民主自由的城市,在那一年泛濫著宵禁和戒嚴的氣氛;精彩繽紛的城市生活,沒有延續到壓抑和恐懼進佔的倫敦。
故事中有一位女士Alice,在戰亂中收養了男孩Billy。日月如梭,26 歲的Billy其心智卻停留在小孩年代,對城市的認知尚未崩壞。一天,Alice 看到街角一位士兵帶著受傷的囚犯,於是打算拿椅子讓他們稍士休息,卻引發一連串悲劇。
坦白說,劇中的細節及對話相當密集,密集得令人有窒息的壓力。大概,這種敘事手法,單以演讀劇本也能以高壓填滿空盪的黑盒。同時,正正因為昏暗的燈光及詳盡的對白,我聽得渾身不自在。就如置身危機滿佈的山嶺,山嶺卻其實沒有對你做過甚麼,只是你自己一個在顫抖。
正是這樣的反差(discrepancy)填滿了整個節目。
中場休息時,我趕緊拾回自己的呼吸,重整自己的經驗,然後我想,那位繼母和男孩若然禱告,他們的心聲應該「向天傾訴,抑或地獄申訴?」
然後,反差繼續。那張載著好意的椅子,徒添罪名;那看似關心的福利官,步步試探;那些記下舊時的圖畫,嘲弄現實。
真實的恐懼,總不如大電影的「大灑狗血」,反而是莫名的冷酷。
劇作者以Billy 的畫作作為分場的名稱。從Alice 一開始的好意,演變成她被政權追迫、調查及帶走。然後,主持人再出場,先讓我們以蠟筆畫出自己的感受,再引導我們搜索枯腸,戴上劇作家的帽子: 要是我們能在劇中某一部分避免悲劇發生,又該怎樣做?
其實這是招很好的「招魂曲」。當我還在沉澱劇中的肅殺,主持人就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將戲劇經驗轉化為問題題目、觀眾感受轉化為解難動力、純粹觀賞轉化為處境解難。
儘管應用劇場的部份,比演讀的環節少很多,卻能有條不紊地整理觀眾的體驗,把虛構的戲劇張力,以及觀眾各自的聯想,轉化為現實中各人需要一同面對的難題。
假如劇場是個想像力的遊樂場,教室則比較像一個集體的修煉道場。要是一個以成人為目標的劇場作品,希望達到以上兩者的結合,大概就是《椅子》的模樣了。
《動物農莊》觀後感
文﹕李嘉敏(台灣香港兩邊走的教育工作者,戲劇教育小粉絲)

2019年3月香港話劇團 與 香港教育劇場論壇合辦「應用劇場萬花筒」,其中一個節目邀請了Theatre OPPZ參與《動物農莊》論壇劇場的演出,讓人看見應用劇場有著怎樣的力量,為大眾提供空間,從不同角度看當今社會議題,並試著尋找改變的可能。
論壇劇場並不是只讓觀眾坐著看戲的演出,觀眾在戲後可以上台取代角色,改變故事結局。當天Theatre OPPZ的《動物農莊》,先由演員們演出一個故事。當天的故事是一個30分鐘、有地道色彩的超濃縮版本《動物農莊》。故事關於一個農場裡面被人類欺壓的動物,終於革命成功、推翻人類管治之後,原本打算共建一個動物自治、糧食共享的農莊,可是天災令動物意識到缺水缺糧的問題。在重建家園的過程中,有一隻想出一項「基建計劃」,遊說其他動物一起建設大風車,並保證有了風車,日後糧食就會自然來。大多數動物都聽信了豬。輾轉間,過程中有豬力慾薰心,為了取得權位,令其他動物淪為奴隸,每天被豬的極權統治,超時工作,吃也吃不飽。也有一些動物中途變節,成為了豬的手下,弱弱相殘去欺壓基層動物。故事裡有一位一直不願從眾的馬,可是孤掌難鳴,最後因為不聽命,結果命喪於豬的極權之下。
故事來到這裡,主持人請觀眾們回想,如果大家不希望故事有這樣的結局,我們希望回到故事的哪個時間點、希望哪個角色作出怎樣的改變,去扭轉情節?觀眾可以輪流提議各樣方案,在主持人的帶領下,以及一眾靈活變通的演員們的急才之中,走到舞台替代演員,作出不同的嘗試,了解方案的效果。觀眾從一開始的被動安靜,到後來漸漸願意舉手提議並走到舞台作出嘗試。大家試過的方案有很多:讓豬從極權者變成體貼員工的老闆、讓馬成為懂勞工權益的工人領袖跟資方討價還價、代入馬的角色遊說其他基層動物一起反抗等等。也有人提議從一開始就要幫助豬遠離利慾,之後的事情就不會發生了。
過程中,有一些特別踴躍的觀眾,討論到故事跟現在的香港社會有很多相似之處。而從這個作品從編劇到主持人的帶領方式,個人也感受到這是Theatre OPPZ很希望觀察能感受到、要知道的以下事情——故事正正在反映香港現況、很有問題、我們要一起改變。有同感的觀察,也會自然連想到豬、馬等不同動物角色與故事情節,可能代表了哪些真實人物和事情。個人觀察到,有這樣共鳴的觀眾,參與得特別起勁,大家提出的觀點都很有意思。例如有兩、三位有走到舞台嘗試改變劇情的觀眾,都有提到,農莊的不公平情況,是一個「共業」,所有動物都有份,包括服從的、反抗但不成功的,或者沉默不反抗的動物,全部人都有份造就極權者。
以上都是很有意思的想法,個人也很同意。不過,因為有出聲、有參與的觀眾,只是少數,因此讓我更感好奇的,大多數沒有出聲也沒有走到舞台參與的觀眾,他們在想甚麼?他們也有共鳴嗎?如果有一些觀眾的觀點不是這樣的,他們會有怎樣的心情和感受?
高牆與雞蛋,Theatre OPPZ《動物農莊》論壇劇場,很明確是站在雞蛋那一邊,也很明顯地,創作者與主持人都很希望觀眾要覺得故事裡的情況是有問題的、豬是壞人、沒作聲的小動物是不行的、改變是必須的。筆者本人的個人信念也類似,這亦是我為何在NGO圈子從事了十幾年公民教育工作的原因。可是,畢竟論壇劇場是開放給背境不同的觀眾、讓大家提出各種立場觀點、作出不同嘗試的空間。如果作品和主持人的觀點太強烈,也期待觀察要同意這些觀點才能參與其中,那麼,就會有點可惜。因為能參與其中的人,很可能都是一早就對議題有理解、跟作品創作單位觀點一致的同溫層,而且討論的觀點也會較單一,失去了開放空間、公民討論的原意。而且,也會讓對議題理解不多、沒甚想法但還是想多聽一點的觀眾,難以在其中安心地參與。
不過,論壇劇場在香港並不多人認識,Theatre OPPZ的《動物農莊》是很好的作品,去讓更多香港人知道「原來看戲可以這樣」、「觀眾也可以走到舞台參演」、「戲劇原來這麼好玩」,也了解到戲劇不是只風花說月、可以跟社會民生息息相關。如果希望能有更多不同立場觀點的觀眾能參與這個論壇劇場,或者,在觀眾參與環節一開始、進入探討「故事是否跟香港現況很相似」、「如何改變」之前,先讓觀眾有機會想一想,自己覺得故事是否有問題,同時對比較無感的觀眾更包容,或者會讓不同立場光譜的人,更能參與探討。然後,再讓覺得有問題的觀眾,想想問題在哪裡、如何產生、誰有份?先讓觀眾對問題根源有更多探索、不改變會有何問題,然後再探討「如何改變」,或者滋養出更多豐富的討論和反思。
《時刻劇場:詩化生命中的珍貴片刻》
文︰吳文基(社區文化發展工作者)
2019年4月13日

重訪回憶的一刻
觀看的時刻劇場當天(2019年3月23日),開場前空舞台的邊緣坐著兩位演員、兩位樂手。開場時主持人先跟現場觀眾打招呼和簡單介紹演出模式,以趕急為基本話題,邀請到第一位觀眾在席上分享故事,然後藝術家們演出回饋。這作為一次示範後,接著很快就有觀眾被邀到台上詳細分享自己的故事。而主持人會明顯地引領分享者聚焦在故事中的特定片刻,仔細而立體地描述出當時發生的事實和主人公的感受,以至現在回想起的想法。
聆聽故事後,舞台上的藝術家──演員/舞者、樂手、影像/繪圖師、燈光師──以他們聆聽到的故事核心,即興以各自的方式營造/演繹/延伸/表演故事中的意象,回饋給分享故事的觀眾。基本上都由最抽象的音樂首先進入,間中吟唱簡單句子;兩位演員以抽象詩化的形體動作,配以呼吸聲或偶爾唸出故事提到的關鍵字,在舞台上即興地運用空間;投影的即時繪畫時而創造故事中的符號,時而為演員創造場景;燈光則較低調地配合,主要為演員的演出範圍調度。幾個演出單位之間很多時候是獨立地呈現故事的某些元素,而某些片刻在台位、身體接觸下連結;最明顯演員同在的時刻,則大多是在塑造故事中描述過的實際場景時出現。片段完成後,主持人嘗試以故事要素連結現場的其他人,吸引出下一個觀眾分享。
主持人引領、觀眾出來分享、藝術家即興演出回饋、回到主持人引領……演出由一個個關於珍惜、惋惜的故事串連,從工作趕急、退休自由、劇場姊妹婚禮、日本分手星空、姊弟遊戲到新任媽媽的擁抱,由藝術家一個個地演繹。最後,藝術家重現不同故事的某些元素,片段式回顧了當天的各個故事作為結尾。劇場內整體氣氛溫馨,幾位分享的觀眾都表示感動甚至哽咽。
以上與一人一故事劇場(一劇場)非常接近,但完全自由演繹的形式,卻又與香港坊間普遍看到,儀式性顯而易見、以整體重現故事的表演略有差異。值得思考的是,這些差異產生了甚麼意義?
時刻的內容、時刻的形式
我曾經以樂師參與時刻劇場的演出,從2012年的形聲影睇(時刻劇場的前身)到2015年的時刻劇場,喜見「時刻」的主題沉澱形成。一個個時刻的碎片,當中的影像、聲音、句子、氣味、觸感,是人每次回溯記憶的錨點,而錨點的重現將會召喚起當下的感官,在主持人引領下重新經歷,與過去的自己對話,讓過去的情感和視角與當下的堆疊,讓講者(同時是觀者)重新敘述/建構自己生命故事,回顧過往的時刻和創造當下在重說/看故事的時刻,對個體的經驗重整來說非常有意義的;同時其他觀眾一起接收到故事、演出的影像和聲音,讓故事的時刻連結社群的共同經驗,亦是難能可貴的。然而對應內容的時刻的意義,演出形式/結構的時刻又是如何塑造?
以我從2012到2019參與演出和觀賞的經驗,時刻劇場為了藝術性的自由創作,在儀式上鬆綁,使在即興演出觀眾的故事時,藝術家們之間的磨合、甚至錯摸的階段,還是時有出現在舞台之上。這個在台上的尋找過程,是默契磨合當中,還是故意保留呈現?尤其是時刻劇場的形式──有別於有很多既定形式的一劇場──多以抽象的形體、音樂和抽象的繪畫碰撞為主,當中的零散的、接近意識流的符號引起的感覺,是容易帶來模糊,但亦同時開放又詩意,就如演後座談會有觀眾指會有看不懂的情況,亦有觀眾指她可以在某些時刻看到個別藝術家的演出而有聯想就已經滿足。創辦人兼演員梁偉傑在演後座談指,觀眾看到舞台上發生的是甚麼,是可以沒有答案的。那抽象的即興創作碰撞,如何能深化對故事裡的「時刻」的呈現?
在我記憶中,在一連串的抽象即興營造氛圍、勾勒故事核心後,演出者常常會完結於擁抱或觸摸等等的動作,作為故事的、強勢的「連結」符號,表現故事主角關係,讓即興安頓;又或者是回到具象的場景──例如今次演出中,姊弟遊戲故事中主角用腳給弟弟做搖搖板的形體和說話、新任媽媽和嬰兒的大小心跳投影等等。這些即興結果提供了影像上的錨點,讓聽過故事的觀眾可以在意象中找回故事中的時刻。
社區中的時刻劇場
讓人好奇的是,這麼大量的抽象演出如何適應各式各樣的觀眾群。根據演後談的研究員伍綺琪指,一劇場的三大核心是「儀式、藝術、社群」。以我理解,一劇場作為社區劇場,很多時應用在完全沒有接觸劇場的社群之中,作為社會介入手段,讓每個人的故事有機會被聆聽,亦能聆聽別人的故事,從而產生橫向的理解和連結。而當中清晰的暖身、儀式、因應故事而選取的演出模式,相信是為觀眾更能掌握演出的結構,從而接收到演出中的呈現和想像。
而時刻劇場,無論是作為一劇場的變奏,還是開拓更自由的劇場形式,在簡化了一劇場的形式後,對應不同的觀眾又會有何不同的策略?抽象的形體、音樂和繪畫,如何啟動觀眾分享的意欲,勇敢地踏出來述說自己的生命?一個個的自由演繹,如何捲動埋藏在內心的情緒記憶?在符號與符號轉換之間,如何呈現在場觀眾之間的社會性連結?容我繼續期待下一次在社區中參與時刻劇場,一探其基於社群所展現出的時刻儀式和時刻美學。
標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