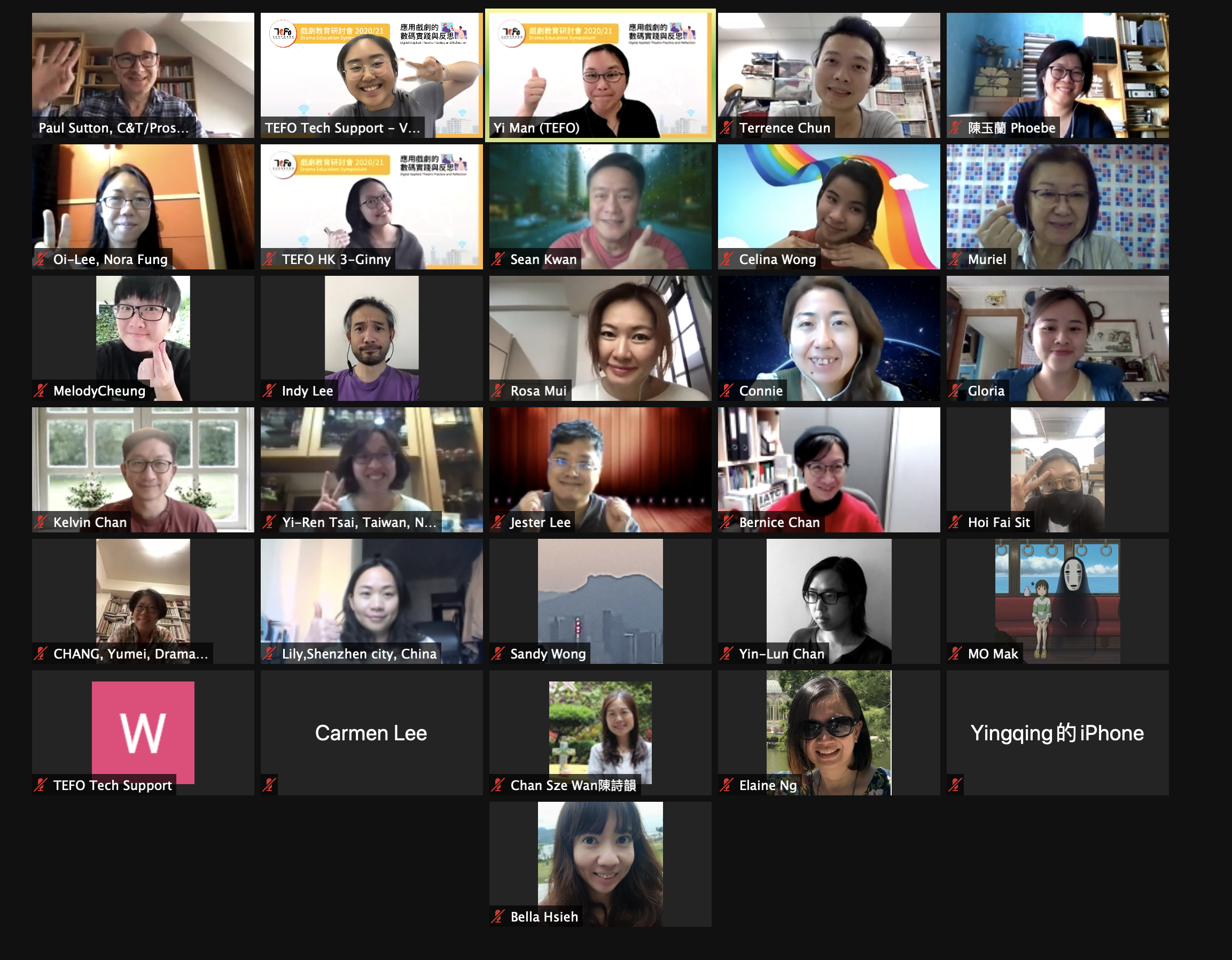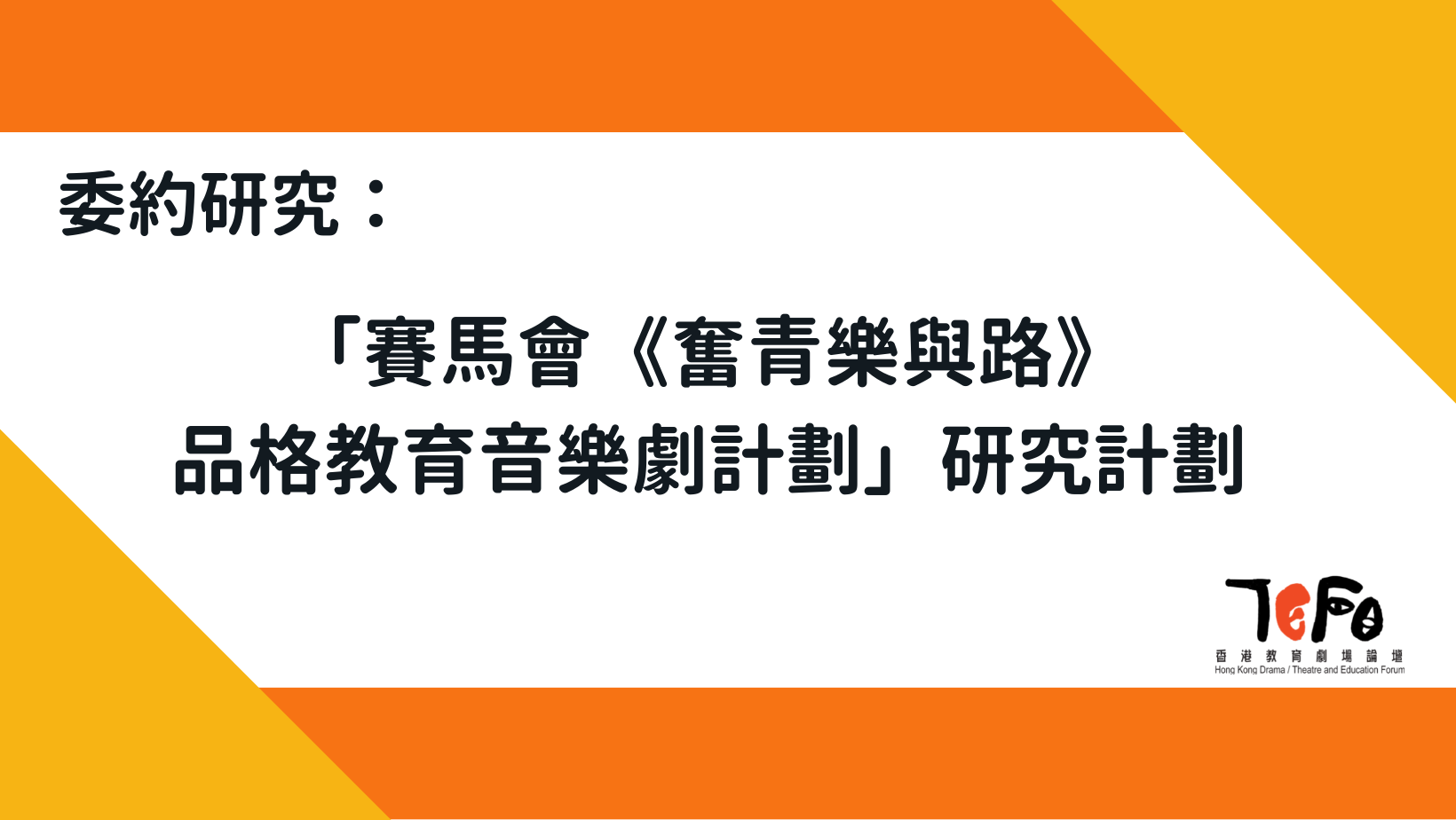做研究是一種觀察和思考世界的工作,需要想像力。
從事教育和戲劇的研究工作這十年間,我不時會碰到前來洽談研究合作的朋友提出的一些疑問。其中一個是:要不要在上戲劇課前給每個學生發一個問卷,測試一下他們懂哪些英文詞彙,然後戲劇課後再填一次問卷看他們的詞彙識多了沒有。另外一個是:要不要在同一個年級裏面區分一些學生做一個控制組(control group)不上戲劇課,跟會上戲劇課的實驗組學生(experimental group)作成效對照。這些問題跟研究策略和蒐集數據方法有關。而更重要是,提問背後反映了對世界的某種看法,包括:認為知識可以通過控制變項做反覆驗證和測試得到;保持距離和中立把實驗抽離自然環境中進行是重要和必須的;以及事物可以用線性因果關連去理解。這種操弄實驗式的世界觀在實驗室以外的現實世界中,依然影響我們;例如現時的中小大學教育現場以至教育政策往往謀求以一個分數來做班級/屆別/學校之間的參照與對比,認為一個百分比或增值指標是最有效和唯一陳述和總結學生學習的方法,足以概括他們整個學習歷程中的主體經驗。
然而,現實世界中,人物關係和情感微妙複雜,人處身其中意欲抽身但不容易;絕非科學驗證式、客觀中立和直線思考的世界觀所能理解和分析。例如,新學年伊始,大學民主牆出現港獨標語和對輕生者家人說恭喜的欠同理心說話,以及在某呐喊大會中發言者對異見人士大喊「殺無赦」,企圖以中國人這身份來動員社會人士參與政治杯葛行動。(註1) 要理解和解釋這些社會文化現象如何產生,則需要理解情感在政治動員上扮演什麼角色,研究者需要具備一些相關和有效的分析工具。文化研究學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提出「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這概念來強調文化評論者不應把思考與情感對立起來,而是需要把存在於兩者之間的連鎖互動與張力梳理出來分析。(註2) 情感結構強調情感並非瞬間即逝或非理性。相反,情感的作用持久,能形塑人的世界觀和理性行為。故此,威廉斯提醒從事文化評論的人士必須有效地探索情感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
回到應用戲劇/劇場這領域,研究的終極目的多元,其中包括弄清戲劇作為教育、賦能或歷史探究等策略的意義所在;或搞清戲劇對於觀眾、學習者/參與者和戲劇人可以發揮的仲介作用和過程;或理清創作者作決定的瞬間受到什麼更深遠的做法和意識形態所影響。研究戲劇藝術的創作、實踐和應用最終是期望為人的處境和社會狀況帶來啟發、新觀點或指出偏見所在,是進行社會探究的另一個進路。蒐集所得的研究數據往往涉及複雜微妙甚至一時無以名狀的情況,跟操弄變項式的科學實驗有本質上的分別,並不能用簡單的是非對錯或成功比率來陳述和分析。應用戲劇/劇場領研究者亦不能套用科學家或化驗師在實驗室內做測試或解剖的工作程序和模式來分析數據。人種誌學者Dwight Conquergood在其影響深遠的論文〈再思人種誌〉中呼籲研究者動用自己的感官認識研究現場的事物,因為身體知覺是研究者的工具。(註3)那麼,應用戲劇/劇場領域中的研究工作如何能做得嚴謹?研究者又如何審視來自研究現場不同形式的數據如訪談、影像、聲音、節奏、情感互動、畫作、文字文本、數字資料等?以上問題就成為應用戲劇/劇場研究工作的重要課題。
Johnny Saldaña專研人種誌戲劇和質性研究,他的著作《Thinking Qualitatively: Methods of the mind》就指出研究者需要鍛鍊質性的思考方法。(註4) Saldaña說,『質性的思考方法涵蓋一系列的思維模式,例如邏輯推理方法如推理和演繹推論,以及運用較藝術性的如象徵意義和隱喻等方式來建構生命。』(註5) 他繼續說,研究者會「刻意地採用不同的鏡頭,濾鏡和角度去察看社會生活,以便發現新觀念和新認知來看待我們正在研究的世界」。(註6)意思是,研究者會把自己的想法和價值觀暫時懸空,借用不同學術領域的視角觀點,專注分析數據的特質。當研究數據與研究者的看法、情緒、信仰,以及行為等出現矛盾或不相容的感覺時,研究者除了確認這個情況之餘,還會把它當作信號標示另一些思考世界的方式浮現了,驅使自己盡可能把這些觀點清晰的描繪並加以分析。因此,Saldaña指出質性的思考是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意思是研究者對自己的認知和思考過程的思考和反思。(註7)
做研究是鍛鍊觀察和思考世界的一種方式。研究歷程中,用質性方法思考的研究者包括從事應用戲劇/劇場研究的人士在內跟科學實驗者不一樣,不是戴防護眼罩保持安全距離,而是配備不同的「鏡頭」,「濾鏡」和「角度」跟數據互動,如舞伴般與數據共舞。舞動中,研究者一邊認識正在研究的世界,一邊反思自己的認知。
註
1. 蘋果日報,(2017年9月17目)。《【革走戴耀廷】曾樹和高呼殺搞港獨者!何君堯附和:唔殺咗佢做咩?》。[網上資料]。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news/20170917/57222043
2. Williams, R. (1977). “Structures of Feeling.” In Marxism and literature, pp. 128-135. Oxford [E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Conquergood, D. (1991). “Rethinking ethnography.”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58,頁180。另可參閱羅婉芬,(2015)。〈走進文化生活〉《亞洲戲劇教育學刊》第五期,頁1-9。
4. Saldaña, J. (2015). Thinking qualitatively: Methods of mind.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5. 同上,頁3。
6. 同上,頁4。
7. 同上,頁5。
標籤: